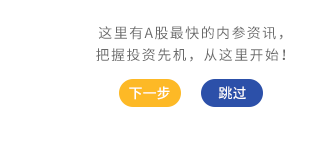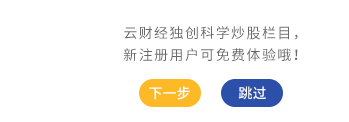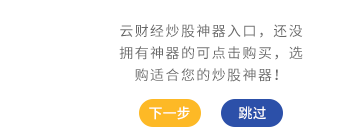央行工作论文呼吁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
 消息收藏夹
收藏
已收藏
消息收藏夹
收藏
已收藏
央行在周二公布的一份工作论文中表示,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工作论文的作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银行的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面临明显约束,不断收紧的金融监管促使大量表外业务回归表内。徐忠称,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他还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
以下为论文全文: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
徐忠
摘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对货币调控方式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我国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须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西方国家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争论,都是针对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而言,而我国仍属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也不稳定,货币调控方式选择和转型须服从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转变,属于全新实践且更为复杂。中国二十多年间接货币政策实践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深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仍需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功能等金融市场体系。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货币价格调控下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今后应在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基础上,加快各项深化改革措施,有效缓解各项约束条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Chines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high growth period, which means the financial policy should de-emphasize the quality targets and measure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the price leverage in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With the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reform was preliminary accomplished, due to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disintermediation as well as the more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market and products, it is urgent to transform China’s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quantity based mode to the price based mode, which is also the necessary step to achieve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first elaborately review the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and practices in the advanced economies. We find out that the quantity and price are the two sides of one coin and it is equivalent of the quantity based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ice based monetary policy in theory. The quantity policy takes effects directly but is prone to contort the price mechanism and individual behaviors. The price policy takes effects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ividuals which
needs a good financial market and interest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monetary policy channe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mode.
The retrospe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satisfied, but we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 modern sense lasts for only around twenty years, after abandoning the direct controls on credit behavior and turning to the quantity indirect policy with the money supply as the intermediate target in 1998. Central bank in China is always confronting the impetus of investment and credit expansion due the traditional growth-led economic mod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al preference to a higher growth rate, there ar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ectors such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vehicles, stated owned firms and hous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The supervisory affaires of the central bank in China were separated. While, due to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dominance of the supervisory ideology, there are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ch promot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hadow banking in recent years and financial risks are accumulated heavily. Although there is enough market breadth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re are still too strict regulations and the market depth is relatively low. The monetary markets and bond markets are still separated, the admittance of the market, esp. the derivative markets are sill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financial products are immature and there are still implicit dual interest track. The exchange rate is still lack of edacity.
So, with the problems above,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still needs quantity measures and we should do lots of preparations to fulfill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The crucial poin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including mature financial micro foundations, good guar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functional financial product markets.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s also promote the interest policy transmission and will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reform in the difficult areas of hedge risks, esp.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governmental debts and supervisory systems,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price-based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which to enhanc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货币数量调控;货币价格调控;高质量发展
Key words: Interest Liberalization,Quantity Monetary Policy,Price Monetary Polic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声明: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Disclaimer: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 publishes research reports written by staff members of the PBC,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cholarly exchanges. The views of these report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PBC. For any quotations from these reports, please state that the source is PBC working paper series.
一、引言
201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标志着历经近二十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这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整个金融改革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过,存贷款利率浮动管制的放开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不再对利率进行管理,而是要由行政手段转向更加倚重市场化工具和传导机制。理论上,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市场利率水平;实践中,无论是利率管制国家还是利率市场化国家,中央银行对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更完整的表述,应是利率由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市场共同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包含着利率形成方式的市场化和利率调控方式的市场化两个不同的维度(纪敏和牛慕鸿,2014)。《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作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原则。随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的取消,利率“放得开”目标基本实现。不过,由于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今后还要在“形得成、调得了”等方面进行大量技术性准备。我国利率市场化正进入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淡化 GDP 增长目标,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实体经济的镜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相适应,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金融调控也要减少对数量目标和手段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已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指出,当前影响货币供给因素更加复杂,不应过度关注 M2 的变化,而是要更多关注利率价格指标,逐步推动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量目标,这既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更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
不过,尽管我国已经淡化货币数量目标,但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拥有较大货币决策自主性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为价格并轨和货币化提供必要空间,还要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实际,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曾很长时期要考虑双顺差的干扰,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以通胀为主的同时始终坚持多目标制(周小川,2013)。可见,正如利率“放得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加复杂,目前利率“形得成、调得了”并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历程,充分认识我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入分析当前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现实约束进而明确改革方向,对今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通过利率价格杠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
(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
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正是在利率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重要性明显下降(Bernanke and Gertler,1995)。各国中央银行在不断修改货币供应目标的同时,不得不多次修改货币统计口径,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效果并不理想(Mishkin,2009)。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效果远不及预期,即使是 Friedman 本人也不得不承这一点(Nelson,2007)。事实上,20 世纪70 年代之前,各国货币政策一直是以利率调控为主(Bindseil,2004),只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使各国在 1960 年代后期普遍陷入痛苦的“滞胀”,金融市场功能和经济平稳发展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各国才不得不接受货币主义主张。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最初就是以利率调控为主,这与其中央银行源自于传统商业银行并一直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放松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下,各国金融市场广度深度进一步提高,以货币总量关系稳定为理论前提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自然是越来越差。正如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 Gerald Bouey 所说的,“我们从未放弃货币总量,而是它们放弃了我们”(Mishkin,1999)。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转向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普遍采用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之一)并在一定规则指导下(隐含地遵循泰勒规则)仅调节短期(隔夜)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Blanchard et al., 2010;Bindseil,2016)。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为此各国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界约束,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Borio and Zabia,2016)。同时,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稳定,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不过,与 2001 年—2006 年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类似,数量目标仅是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第二位操作目标,为恢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刺激经济复苏而保持超低(零)利率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操作目标(Bindseil, 2004,2016)。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美英欧等主要央行都开启或着手加息缩表并重回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中国的间接货币政策:由数量到价格的调控方式转型
我国符合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实践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主要受到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客观因素制约,也与计划经济更倾向于数量调控的政策惯性和决策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周小川,2004)。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巨大外部冲击考验,根据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开展货币调控,成功应对了通货紧缩、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及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金融调控环境变化等严峻挑战。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为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由计划直接管理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依靠计划手段人为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运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宏观调控框架(周小川,2013),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业,银行是最主要金融机构,主要发挥监督资金使用的社会出纳功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拨改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期间我国金融资源价格及其配置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即使重新组建的专业银行也都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张杰,2011)。1984 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管理直接控制方式进行货币信贷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 1994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缩小信贷规模管理范围,公布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 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并将现金发行转为监测指标。同时,我国还将各地分散的拆借市场统一为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由于银行间市场属于同业批发市场,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率先放开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利率。1998 年,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正式实现由直接控制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转型(张晓慧,2015)。
2、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
1998 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最主要的常态化货币调控手段。在当时通货紧缩的背景下,主要通过逆回购投放基础货币;2000 年针对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贷款而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以及外汇占款迅速增长,引入正回购业务吸收市场流动性;2001 年下半年根据当时通货紧缩形势,在进行逆回购的同时大量开展现券买断业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戴根有,2003)。
2001 年底加入 WTO 之后不久,至少从 2002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除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外,我国面临长达近十年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局面。由于正回购和现券卖断业务受到中央银行持有债券资产规模的约束,2003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并将其作为对冲流动性的最主要手段。随着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失衡加剧,我国开始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充分发挥其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将存款准备金率打造为常规的、与央票发行相互搭配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迅速锁定了长期流动性,有效地降低了货币乘数和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方式优化信贷投放结构和节奏,结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和人民币稳步渐进升值,有效应对长期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较好实现了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张晓慧,2011)。
3、经济新常态和流动性格局变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
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不久,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新常态,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占款和流动性过剩格局明显改观。从 2011 年开始,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首次回落并始终处于国际认可的 4%以下合理区间。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态势,2012 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首次出现自 1999 年以来的小幅逆差,2014 年 2 季度末外汇储备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直至 2016 年 4 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始终保持逆差。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并在基本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为此,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央票发行并重启逆回购操作,2013 年以来开展了包括 SLO、SLF、MLF、PSL 等在内的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和中长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工作,改进存贷款比和准备金考核,调整再贷款分类体系,完善央行抵押品框架,将公开市场操作由每周两次扩展至每日操作,有效确保了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强了市场利率引导能力,为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张晓慧,2017)。
4、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在货币政策转向间接调控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就积极发展金融市场,放松利率管制,在 2000 年左右基本实现了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2004 年实现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管理模式,通过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渐进双轨制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易纲,2009a)。不过,尽管我国通过央票发行有效促进了货币市场发展和期限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完善,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利率调控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晓慧,2011), 2007 年正式引入 Shibor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2008 年 10 月还扩大了按揭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但在应对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繁重调控压力下,2004 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缓慢。
我国货币决策者很早就意识到,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货币数量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价格传导效率,而价格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将不可避免引发数量扭曲(周小川,2004)。因此,在以数量调控为主的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十分重视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非常注意“量”与“价”的平衡(张晓慧,2015)。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流动性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极大增强了中央银行调控流动性的主动性,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宏观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2 年 6 月,我国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2013年7 月基本取消贷款利率管制,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限制。
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M2 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易纲,2018a)。事实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 M2 中间目标的问题,2011 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2015 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 2016 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 M2 趋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 M2 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
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和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固定收益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公司信用类和金融机构债券均列全球第二),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广度和必要的市场深度(潘功胜,2016)。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敏感性显著增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渠道日益畅通有效(Kamber and Mohanty,2018)。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利率引导进行了大量技术性准备和理论研究工作(牛慕鸿等,2017),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周小川,2013)。
三、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困境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由计划人为干预逐步转向总量为主的宏观调控。借鉴国际经验与立足国情创新有机结合,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我国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经验(周小川,2011)。不过,也要认识到,虽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日益复杂,货币政策亟须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转轨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各阶段宏观调控主要矛盾和特征并不一致,不同时期政策的着力点各有侧重,不同类型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从二十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金融仍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着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有效,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经济中仍存在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央行货币政策始终是易松难紧
1998 年之前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信贷调控一直饱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就实行了国际通行的准备金制度。不过,在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下,准备金制度的着眼点是让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相当数量的信贷资金并进行结构调整,信贷规模主要按地区和项目信贷计划的方式进行管理(周正庆,1993)。但是,信贷规模管理制度设想需要一个前提,即充裕的资金只能以超额准备金方式流向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地区间进行信贷规模调剂,这比较符合 1980 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实际情况。随着各地区拆借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有效分配信贷资金: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存款充裕地区(主要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要求增加再贷款和信贷规模;存款少的地区由于其仍然拥有贷款额度,贷款计划往往与实际存款不匹配,中央银行不得不为其追加再贷款以确保其正常运行;较高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也加大了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倒逼压力。而且,当时信贷政策的透明度较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地方政府干扰较多。因此,信贷规模管理实际上无法有效抑制信贷冲动,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并埋下了经济过热隐患。正是在此背景下,1990 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由信贷直接管理逐步转向间接调控,1993 年将各地分支机构再贷款发放权集中统一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4 年停止对财政透支和专项贷款,1997 年决定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以避免地方政府干扰,最终于 1998 年完全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数量为主间接货币调控(易纲,2009b)。
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形成了 GDP 导向的“锦标赛”增长模式(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化工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2004 年土地全面“招拍挂”后,土地收益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基建和重化工业投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而房地产又有着“大而不倒”的软约束特征。因此,在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导向下,我国存在着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有着强烈的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内在动力(纪敏等,2017)。1990 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信贷规模管理失效,很大程度上就与地方过度投资倒逼再贷款密切相关。
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双顺差,为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应适度压缩国内投资。但是,“锦标赛”模式下各地投资冲动无法得到有效抑制,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期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扩张,货币政策更加易松难紧。事实上,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2006 年底中央就提出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经济刚刚走出通缩和非典冲击阴影后,明确提示信贷过快增长风险,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 。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等进行适度从紧稳健货币调控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宏观审慎政策手段。2004 年对不同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2005 年适度提高了不同类型房屋首付比例;2007 年开展具有激励相容性质的央行票据定向发行工作。
不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也转向适度宽松。应当说,危机后必要的刺激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增长导向和传统增长模式下,刺激政策手段粗放调整过度,难以有效退出,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早在 2009 年年中就注意到经济过度刺激苗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动态微调”,2010 年连续上调准备金和基准利率逐步退出适度宽松政策。但是,在 GDP 增长目标导向和软预算部门压力下,信贷需求仍非常强烈。特别是,尽管 2011 年以来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但市场仍存在着强烈的新一轮刺激预期。为有效打破各方政策放松预期,2013 年 2 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发行央票并对部分到期的 3 年期央票进行续做,积极与市场沟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性政策工具成功化解了货币市场波动。
尽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趋势性下降,但为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促进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等政策需要,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通过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降息引导降低金融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效益和房地产市场明显下滑,2014 年以来我国一度出现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张平,2015),各方政策放松预期强烈。而且,虽然 2014 开始我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但地方政府利用 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等方式进行大量隐性负债。2015 年我国发生股灾,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经济的担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于 2015 年至 2016年1 季度分别进行了五次定向降准政策和五次普遍降准,为顺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应当看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避免大水漫灌依赖货币信贷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但利率政策属于反映资金价格的宏观总量货币手段,无法有效调节结构性问题,并不完全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上升,根据 IMF的测算,2016 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 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僵尸企业和低效投资项目大量挤占金融资源,被总量问题所掩盖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空间非常有限,而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利器”,资产负债表效应和信号意义较强。在潜在增速趋势性下行与经济周期性下滑交织重叠背景下,大幅降低准备金要求将释放强烈宽松政策信号,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明显不符。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逆回购业务、SLF 和 MLF 等方式弥补市场流动性数量缺口,始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特别是,随着 2015 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守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不进行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仅是结合普惠金融发展于 2018 年 1 月进行一次定向降准。
另外,预算软约束部门由于隐性担保人为降低了信用溢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支持,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融资(纪洋等,2016)。虽然理论上任何预算软约束问题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并可通过合理的定价予以弥补(罗长林和邹恒甫,2014),但如果完全依赖价格机制,正规融资利率必须上升至足以弥补风险溢价的高水平,这将推高非正规融资成本,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更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纪洋等,2016)。因此,在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取消后,我国并未立刻转向利率价格调控,而是仍通过准备金、广义信贷等数量方式控制债务和杠杆率的过快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未处理好监管与央行的关系,监管与行业发展职能没有分离,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倒逼央行政策放松
1997 年之前,虽然我国一直有金融业的主管部门,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负责金融管理的同时,明显受到地方政府的倒逼和掣肘,无法真正关注金融风险。金融业处于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状态,银行可直接向股市参与者发放贷款,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波动剧烈。同时,国有企业三角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银行为消化“拨改贷”等政策性负担开展大量高收益投机业务,各地“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迅速蔓延,严重干扰了正常经济金融秩序。为此,1993 年 7 月我国开始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1993 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将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特别是,1995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银行不得为财政透支,商业银行实行比例管理;1996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并承诺遵守《巴塞尔协议》,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各方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在此期间,我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这些行业的监管。同时,针对 1996 年由于大量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引发的股票市场行情异常过热,中央明确要求银行将资金全部撤出交易所市场。最终,1997 年底首次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这为化解再贷款冲动,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1998 年-2002 年的通货紧缩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大量再贷款,国家还发行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大量问题、前期过快放贷和风险意识淡薄等原因,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非常庞大,资本充足度严重不足,海外有机构甚至指出国有银行已接近技术性破产边缘。银行惜贷异常严重,金融信用媒介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进一步加剧了通缩局面。直至 2001 年底加入 WTO 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才于 2002 年下半年逐步走出通缩阴影,经济进入强劲上升轨道。
2003 年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格局。但是,金融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理顺,监管政策始终倾向于本行业的发展。2003 年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对金融体系进行“在线修复”,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开展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激励相容方式进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过,随着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逐步消化和改革后经营绩效的明显好转,监管部门逐渐偏离机构审慎监管,更加关注本行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未能有效调控银行信贷投放,2010 年货币信贷增速大幅突破年初目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初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开展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力图控制银行表内信贷过快增长。不过,出于行业发展和部门利益的考虑,监管部门仍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以规避准备金和信贷规模约束。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都竞相放松监管要求。由此,针对信贷规模管制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迅猛发展。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 GDP 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20%迅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31.2%,远快于同期货币信贷增速。而且,2014 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呈现出结构化、复杂化趋势。在行业发展理念下,监管部门并不重视整体系统性风险,甚至为了本行业发展而降低监管标准,从而引发“监管竞次”,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并存,影子银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集聚更加严峻。2015 年由于对场外配资等违规行为监管不力,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再贷款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下行和不良资产逐渐暴露,银行不得不提高风险资本占用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双降”曾是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为此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创新,各微观监管部门纷纷降低监管标准并形成大量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监管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2014 年以来银行负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脱媒明显上升(李宏瑾和苏乃芳,2017)。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与非银机构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各种嵌套,使得负债端变得极为复杂,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在资产运用方面,资管、同业等表外业务监管标准和风险权重相对较低,银行实际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严重不足。2014 年—2016 年,结构化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上升,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Ehlers et al., 2018)。
由于多层嵌套使得金融交易更加复杂,市场产品价格无法真正反映真实信用风险溢价, 利率传导和利率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在缺乏必要的监管职能和良好的监管协调情况下,为控制影子银行信贷扩张和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于 2016 年初将存款准备金动态管理升级为宏观审慎政策评估(MPA),针对广义信贷规模进行逆周期调控,形成了“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框架。2017 年初和 2018 年初,分别将银行表外理财和资产规模 5000 亿以上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 MPA 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机结合,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
金融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管制,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严重制约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影响利率政策传导效率
1990 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的完整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随着银行体系的恢复发展而在不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19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陆续组建了用于调剂银行资金盈余的同业拆借市场,这对丰富交易品种、提高银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各地拆借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资金交易越来越活跃,但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管理程度也不尽一致,分散各地的拆借市场成为 1990 年代初金融“三乱”和借短放长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6 年初将各地资金市场整合为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有效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发展,为 1996 年 7 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在 1996 年开始尝试在交易所债券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由于为做大市场交易而放松监管和风控严重滞后,1995 年 2 月爆发了“327 国债期货”事件,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几乎停滞,银行在交易所的大量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致使当时股票市场异常过热。由于交易所市场债券品种和数量的限制,在 1996 年尝试了几笔总量仅 20 多亿元的交易后,央行不得不停止了公开市场操作。为此,1997 年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经验,建立了场外交易模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必要的操作平台和坚实的市场基础(戴根有,2003)。针对当时中央银行国债现券数量规模的限制,我国在 1998 年重启公开市场操作时,将业务扩展至政策性金融债等高等级政府支持性债券,在促进这类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利率的市场化。
随着 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特别是 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需要足够的债券资产进行流动性对冲操作。不过,由于财政部门国债发行仅考虑自身融资需求,国债期限过长、数量偏少且国债发行并不规律,国债市场广度深度无法满足央行和金融机构交易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方式进行流动性对冲。针对发改委和证监会对企业信用债管制过严导致市场发展受限,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005 年和2008 年引入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市场。同时,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2007 年成立了银行间市场交易商量协会,通过市场自律方式促进债券市场规范发展,实行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制。全球金融危机后,借鉴国际经验于 2009 年成立了以中央对手为主的集中清算的上海清算所,进一步规范了债券市场发展。银行间市场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有关部门放松过严的市场管制,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就上升至全球第三位。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发展并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市场分割、深度不够等问题,影响到了市场利率的有效形成及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具体表现在:
一是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仍被人为分割。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一直存在着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由于两个市场准入和监管存在明显差异,市场价格分化明显,这进一步助长了市场的监管套利。特别是,交易所市场信用风险溢价较高,利率水平和波动都明显高于银行间市场,干扰了市场预期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例如,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逆回购、SLF 和 MLF 等工具有效引导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水平,并在2017 年5 月推出了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和以7 天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但 2016 年底以来,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如 DR001和DR007)与全部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利率(R001 和 R007)价格背离趋势明显,这也反映了影子银行规模扩大和金融风险集聚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市场分割进一步加剧。
二是金融市场交易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利率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1997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很早就意识到市场交易规模、品种和衍生品市场对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和间接货币调控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市场参与主体、产品和衍生品创新的发展。但是,微观监管部门对金融主体参与衍生品市场仍存在过于严格的准入限制,衍生品市场主要仍以交易类型为主,针对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发展滞后。从国际上看, 1970 年代以来,作为风险管理主要手段的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衍生品交易量远远超过基础资产规模。根据 BIS 统计,2017 年上半年美元和日元债券利率衍生品交易额分别为 156.2 万亿美元和 40.8 万亿美元,均相当于债券基础资产的 3.5 倍左右。2017 年中国利率衍生品交易达到历史最高的 14.4 万亿元,但仍不到全部债券市场基础资产的 20%,市场深度仍待提高。
三是金融市场产品发展仍待丰富完善。目前质押式回购是我国货币市场最主要品种,基于信用的买断式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但质押式回购需要冻结债券流动性,而且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来源主体,债券换手率较低,这不利于债券市场价格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有效畅通金融市场和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的重要途径。2005年正式开启的资产证券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暂停,2012 年重启后主要是以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为主,而非国际通行的按揭或消费信贷,产品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很难准确估计产品违约概率并合理地定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深化发展(徐忠,2015)。
四是由于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依然不足,在放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后,我国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过渡性措施。由于我国银行存贷款定价和利率管理长期依靠存贷款基准利率,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相当于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易纲,2018b),这将影响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降低货币价格调控的有效性。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须深化,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依然有限,影响了利率调控的政策自主性
利率和汇率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汇率的灵活调整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顺利实现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产出和物价等内部均衡而非外部均衡,货币的外部目标也应服从内部目标。我国货币政策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中间解安排,总体上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这也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经验(徐忠,2017)。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中间解安排将越来越不稳定,角点解将成为唯一的稳定安排(易纲和汤弦,2001)。灵活的市场化汇率作为经济安全阀和稳定器,是利率市场化和自主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易纲,2013)。改革开放后,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1994 年和 1996 年我国先后完成汇率并轨和经常账户开放,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当时既定的改革目标。但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延缓了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周小川,2015)。不过,2005 年 7 月开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暂收窄波动浮动外,我国始终坚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 年 6 月我国再次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中间价浮动空间由 0.3%逐步扩大至目前的 2%。2015年8 月我国进行了“收盘汇率 一篮子货币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由于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原因,2015 年 2 季度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再加上美国加息政策预期,我国存在较大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为此,2015 年底我国开始将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范畴;2017 年 5 月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反映宏观基本面情况。随着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明显好转,目前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逐步回归中性。2017 年 9 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2018 年 1 月将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调至中性。
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市场化汇率水平,但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仍是加快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和清洁浮动,始终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易纲,2016)。不过,我国外汇市场广度深度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和清洁浮动。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市场品种、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陆续推出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但是,根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求,我国一直强调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实需原则,所有外汇交易必须有真实、合规的贸易或者投融资背景。在资本跨境流动仍存在较多限制,经常账户持续顺差情况下,企业外汇需求净头寸方向变化不大。在实需原则下,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外汇交易头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银行又都是风险厌恶者,根据企业外汇需求的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基本一致,这不利于外汇价格的发现。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适度的投机,就容易影响外汇市场功能的发挥。境外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即 NDF)之所以能够随时出清,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既有套保的、也有投机的,市场才有足够的流动性。正是由于实需原则的限制,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仍然有限。根据 BIS 统计,2016 年 4 月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中,在岸市场仅占全球人民币日均外汇市场交易量的 36%,其中,在岸人民币外汇即期和衍生品日均交易量占比分别为 43.6%和 32.3%。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由信贷直接控制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金融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以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取消为标志,最终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面临由数量为主到价格为主的第二次重大转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由数量方式人为补足经济的短板转向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化方式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益。2018 年,我国不再设定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的量目标,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监测目标,这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政府非此仅彼的怪圈。
(一)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是指某个具体的金融产品市场及其组合,而是由金融市场微观主体、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共同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至少要包含金融市场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制度保障和金融市场产品体系三个方面。在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面临的政府过度关注增长目标和预算软约束、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正是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问题的具体表现。
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包括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两个方面。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和国有企业等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资金需求过度旺盛,通过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因此,只有政府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真正在良好公司治理下按照风险资本约束、根据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进行融资行为,真正硬化预算约束,市场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才能够更为理性,货币政策也不再受到倒逼扩张的压力,市场利率水平才能够回归合理水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相对缓慢,一定程度上也与依赖外贸的传统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从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正是在过度关注行业发展的监管政策导向下,刚性兑付难以真正打破,利率定价无法反映真实的信用溢价;金融机构更关注规模的扩张,而不是针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开展精细化的产品管理。只有综合权衡风险和收益,围绕市场资金需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才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政策才能够通过利率政策价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金融市场制度保障方面,由于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监管部门并不是真正根据金融功能和行为防范风险,针对规避管制和监管套利的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多层嵌套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利率水平上更多地叠加了不合理的制度成本而非正常的风险溢价,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和政策效果也因而大打折扣。
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方面,目前我国已具备了足够的金融市场规模和广度,但金融市场发展深度方面仍然相对不足,产品功能仍须健全完善。由于金融制度体系的缺陷,以机构准入替代产品的市场发展,大量的所谓市场创新更多地是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的产物,而真正市场化的具有充分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品)不够丰富,微观金融主体利率定价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始终无法真正受到市场的检验。在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条件下,金融市场产品定价大多以固定利率为主。今后应大力培育完善 Shibor、国债收益率等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浮动利率产品提供坚实可靠的定价基础,切实增强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外汇市场深度有限(特别是外汇衍生品市场)也与过于严格的市场管制密切相关。
深化金融市场发展,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
正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微观主体、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不得不仍依赖数量调控手段,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产出物价等的平稳发展。不过,也要认识到,过度依赖数量调控方式将降低利率传导效率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马骏和王红林,2014),过度依赖结构性政策容易换取价格机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易纲,2006)。而且,传统的货币数量调控模式下,货币数量信号频率较低,对经济形势的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操作等有关链条相对较长。与之相比,由于金融市场冲击对流动性和利率的扰动更加频繁,货币价格调控与金融市场关系更加紧密,这也要求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加快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
五、结论性评述
理论上,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充分有效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是等价的。不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现实条件对货币“量”和“价”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看,各国普遍经历了由“利率到数量再回归利率”循环往复的过程,各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货币数量目标制的货币主义实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仅是短瞬即逝,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过程表明,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经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滞胀”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经济深陷危机泥潭,各国才不得不由利率调控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而正是在高通胀压力下,各国不得不纷纷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使得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在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明显优于数量调控,各国才重新回归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利率调控。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巨大冲击和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数量调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
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一直都是在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即我们所谓高质量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脱胎于计划经济,属于全新的政策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符合转轨初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产出物价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政策经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在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推动下,我国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亟须向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等利率操作模式基本完备,我国已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不过,正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货币政策仍需要依赖数量调控方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各项约束条件的有效缓解,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充分条件将更加成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终将水到渠成。
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则是通过价格杠杆,在金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正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今后应当在有效发挥数量调控优化结构的同时,做好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要综合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兼顾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需要,加快推进各项深层次改革,努力做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机制改革,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发展更多的浮动利率产品,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 新闻标题 | 时间 | 消息来源 | 新闻热度 |
|---|